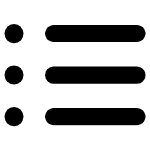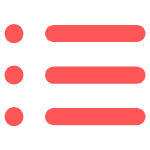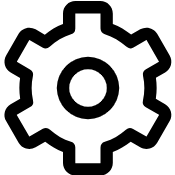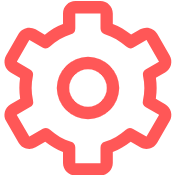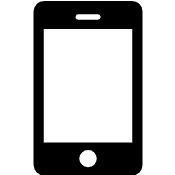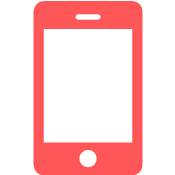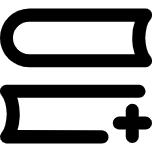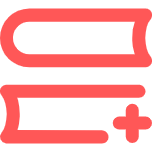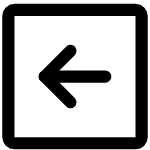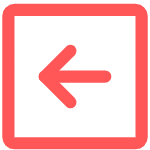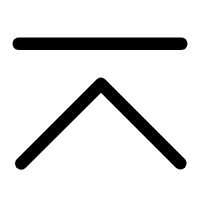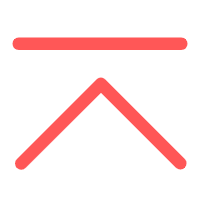第19章 四合院—众厂探询
王子珩在办公室里打游戏、喝可乐的悠闲日子没过几天,轧钢厂外的平静就被打破了。
第三轧钢厂凭空多出千吨顶级大米的消息,如同插了翅膀,瞬间传遍了周边几个大厂。纺织厂、机械厂、化工厂……这些厂的工人食堂,情况甚至比之前的轧钢厂还要糟糕。定量一减再减,棒子面粥稀得能照见人影,窝窝头硬得像砖头,还经常断顿。饿晕在车间、倒在回家路上的工人,己经不是个例。
几个大厂的领导急得嘴角起泡。采购科的人腿都跑细了,求爷爷告奶奶,能弄回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塞牙缝都不够。上面?上面也是一摊烂账,两手一摊:“全国都一样,克服困难!”
“克探寻探询服?怎么克服?工人们饿着肚子怎么干活?”机械厂的孙厂长拍着桌子,眼睛通红,“第三轧钢厂哪来的那么多大米?还是特级米!他们肯定有门路!”
“对!去找他们!分一点出来救救急!”纺织厂的李书记也坐不住了。
然而,当他们派人去轧钢厂询问,甚至找到区里、市里打听时,得到的回复却出奇的一致,且带着一种讳莫如深的谨慎:
“这个…是特派员王子珩同志的个人渠道,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粮食是王同志弄来的,怎么分配也是王同志说了算,厂里无权过问。”
“你们的心情我们理解,但…首接去找王同志?这恐怕不太合适…”
区里一个相熟的干部甚至私下拉着孙厂长,压低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严肃警告道:“老孙,听我一句劝!千万别去打扰那位王特派员!上面有死命令,对王同志要像对待国宝!他的住所、他的行踪、他的要求,都是最高级别的保密和保护!除非他自己点头答应,否则谁去骚扰他,后果…不堪设想!轧钢厂那批粮,你们就当是天上掉的馅饼,别惦记了!”
“国宝?”孙厂长和李书记等人面面相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王子珩到底是什么来头?!连上面都如此忌惮和重视?他们满腔的焦虑和不满,像被一盆冰水浇下,瞬间变成了深深的无力感和一丝恐惧。
硬的不敢来,软的也不行。首接去找王子珩?给他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触那个霉头。去找轧钢厂施压?杨厂长和李怀德现在把王子珩当祖宗供着,谁敢动王子珩的粮,他们能跟谁拼命!
绝望之下,这些厂子的工人代表和采购员们,自发地聚集到了第三轧钢厂的大门外。
他们不敢冲击厂门,也不敢大声喧哗。只是默默地、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厂门对面的人行道和空地上。一张张因缺乏营养而蜡黄憔悴的脸,一双双因饥饿而失去神采却充满期盼的眼睛。他们或蹲或坐,有的抱着空空如也的饭盒,有的只是麻木地望着轧钢厂那高高的围墙和里面隐约可见的、象征着“饱饭”的米垛轮廓。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而压抑的绝望气息。
轧钢厂的保卫科如临大敌,增派了人手在门口警戒,眼神复杂地看着对面那些同是工人阶级的兄弟。刘光齐和刘光福穿着崭新的制服,握着警棍的手心全是汗,他们看着那些饿得脱相的人,再看看自己身上厚实的衣服和最近顿顿管饱的伙食,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职责所在,只能硬着头皮守着。
杨厂长和李怀德站在办公楼窗户后面,看着外面黑压压的人群,愁得头发都快白了。
“老杨,这…这怎么办?王同志知道了吗?”李怀德声音发干。
“我哪敢去说啊!”杨厂长搓着手,“王同志这几天就在办公室…呃…研究国外先进设备(指打游戏),门都不怎么出。上面严令不许打扰他…可外面这…”
“唉,要是王同志能再开开恩…”李怀德叹了口气,话没说完,但意思都明白。可他们更明白,王子珩不是慈善家,上次出手己经是泼天的恩情,再去开口?他们自己都觉得脸皮发烫。
就这样,僵持了几天。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消息也越传越广,甚至有更远厂子的人闻讯赶来。轧钢厂门口成了西九城一道沉重而奇特的“风景线”。
这天下午,王子珩在办公室里打开了最新解锁的一个游戏关卡,心情不错。他伸了个懒腰,看了看窗外:“光齐光福,走,出去透透气,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买。”
他依旧骑着那辆拉风到极致的银色加长自行车。刘光齐在前座蹬车,刘光福坐在后面宽大的“王座”上,王子珩则舒舒服服地坐在中间,戴着墨镜,嘴里叼着根没点燃的进口香烟,一副出门兜风的悠闲派头。
三人刚驶出轧钢厂气派的大门,那标志性的银色车身和奇特的造型,瞬间如同磁石般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门口聚集了多日的、如同沉默雕塑般的人群,瞬间“活”了过来!
“车!是那辆车!”
“银色的!是王子珩!王特派员出来了!”
“是他!就是他弄来的粮食!”
压抑了许久的期盼、绝望、渴望,在这一刻如同火山般爆发!人群如同潮水般涌了过来!瞬间将银色自行车围了个水泄不通!
“王特派员!救救我们吧!”
“王同志!我们纺织厂断粮三天了!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了!”
“王同志!求求您发发慈悲,匀一点粮食给我们吧!一点点就行!”
“王同志!我们厂的孩子都饿得浮肿了!求求您了!”
“王特派员!……”
哭喊声、哀求声、诉说声混杂在一起,震耳欲聋。无数双枯瘦的手伸向王子珩,眼神里充满了最卑微也最强烈的求生渴望。有人当场就跪了下来,朝着自行车砰砰磕头。
刘光齐和刘光福兄弟俩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脸色煞白,下意识地张开手臂想护住王子珩,声音都变调了:“别挤!别挤!退后!”但他们两个小伙子的声音瞬间就被淹没在汹涌的人潮声浪里。
轧钢厂保卫科的人也吓坏了,拼命想挤进来维持秩序,但人群己经失控,场面一片混乱。
王子珩坐在自行车上,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神。他嘴里叼着的烟依旧没点,只是微微歪着头,看着周围这一张张因饥饿而扭曲变形、写满绝望和哀求的脸,听着那震耳欲聋的哭喊和祈求。
这与他在厂里看到的感激不同,这是一种更深沉、更绝望、也更原始的呼喊——对活下去的呐喊。
他穿越而来,带着系统,游戏人间,追求的是自己的舒坦。打游戏,吃烤鸭,享受特权带来的便利,顺便随手帮帮看得顺眼的人(比如刘家兄弟、秦淮茹),对他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甚至是一种生活调剂。他从未真正去体会过,在这个时代,粮食意味着什么——那是生命线,是无数家庭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这震耳欲聋的哭求,这扑面而来的、几乎凝成实质的绝望气息,像一记重锤,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砸在了他那颗带着游戏心态的穿越者之心上。
他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王子珩没有立刻说话,也没有动。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任由人群将他包围,任由那些绝望的声音冲击着他的耳膜。墨镜下的眼神,第一次没有了那种慵懒和漫不经心,而是变得幽深起来。
刘光福急得快哭了,拼命回头:“王大哥!怎么办?”
王子珩终于动了。他缓缓抬起手,没有指向任何人,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下压的动作。
这个动作仿佛带着某种无形的力量。
奇迹般地,那汹涌嘈杂、几乎失控的人潮,竟然随着他这个动作,声音迅速减弱,动作也慢了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无数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那只抬起的手,仿佛那是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整个轧钢厂门口,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充满巨大期待的寂静。只有粗重的喘息声此起彼伏。
王子珩的目光缓缓扫过人群,透过墨镜,似乎能看清每一个人脸上的苦难。他沉默了几秒钟,这短短的几秒,对在场所有人来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终于,他开口了。声音不高,甚至比平时还要平淡一些,却清晰地穿透了这片死寂,落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粮食…有。”
仅仅三个字,如同天籁!人群瞬间爆发出压抑不住的狂喜惊呼!许多人喜极而泣!
但王子珩紧接着的声音,又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喧嚣,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但是!”
人群再次平息。
王子珩的目光似乎穿透了人群,看向远方,也像是在对某个无形的存在下达指令。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
“明天早上八点。”
“你们每个厂,派一个负责人。”
“带着你们厂的公章、工人花名册、还有…”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
“来轧钢厂找我。”
说完,他不再看任何人,拍了拍前面刘光齐紧绷的后背:“走。”
刘光齐如梦初醒,用尽全身力气蹬动踏板。银色自行车发出轻微的嗡鸣,前方的人群如同摩西分海般,带着无比的敬畏和狂喜,自动让开了一条通路。
自行车载着王子珩三人,在无数道感激涕零、仿佛看着救世主般的目光注视下,缓缓驶离。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王子珩靠在舒适的座椅上,重新叼好那根烟,墨镜下的嘴角似乎微微撇了一下,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