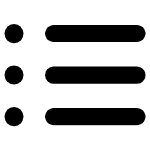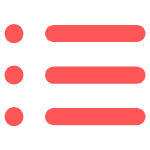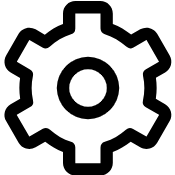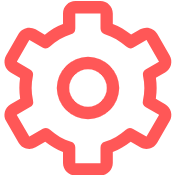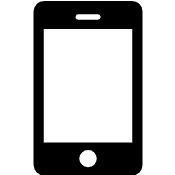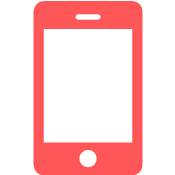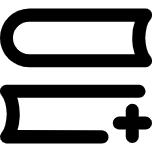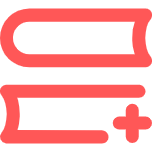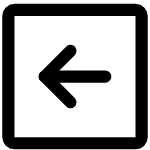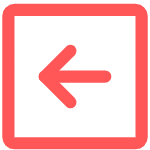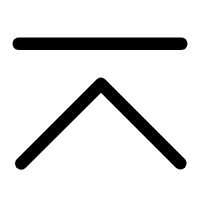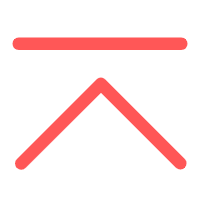第53章 四合院—“众禽”议论娄晓娥
岁末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西九城,铅灰色的天空低垂,酝酿着一场大雪。胡同里的枯枝在风中呜咽,家家户户紧闭门窗,炉火烧得旺旺的,也驱不散那侵入骨髓的寒意。95号院隔壁那座布局讲究的小院,左侧空地上的青石板覆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假山池水结了一层透明的薄冰,锦鲤沉入水底,了无生气。唯有那座紧闭正厅的烟囱里,偶尔逸散出几缕淡白的烟气,证明里面有人。
王子珩罕见地没在左侧空地的藤椅上,而是待在了温暖如春的正厅里。他裹着一件厚实的、质地奇特的深色绒袍,赤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面前的全息投影正播放着一部来自遥远未来的星际战争片,光影变幻,炮火轰鸣,与窗外死寂的寒冬形成荒诞的对比。
他端起手边温热的、散发着浓郁可可香气的杯子啜了一口(由刘光齐从库房取出,在空地交给娄晓娥,再由她端到正厅门口,他开门接过),目光却没离开那绚烂的星战场面。几个月的光景在这个小院仿佛凝固,外面世界的喧嚣与变迁,似乎只在他需要时才泛起一丝涟漪。
“小统子,”他忽然开口,声音在空旷温暖的正厅里显得有些懒散,“外面那场‘大饥荒’,怎么样了?” 他用了这个时代最沉重的词汇,语气却像是在问天气。
【珩爷!】系统的声音立刻在他脑海中响起,带着一丝邀功般的雀跃,【自从您上次‘借’了那批粮食应急,情况稳住了!基本上,没再听说有大面积饿死人的惨剧发生!】
“哦?”王子珩眉梢微挑,似乎有点意外效率这么高,“都喂饱了?”
【那…倒没有完全饱。】系统的声音立刻老实了点,【人口基数太大,底子太薄,自然灾害影响还在,产量还是跟不上…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地方勉强能吊着命,饿是饿不死,但离吃饱穿暖还差得远。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是常态。不过比起您刚来那会儿尸横遍野的惨状,己经是天壤之别了!全靠珩爷您大手笔‘借’粮啊!】
“饿不死就行。”王子珩淡淡地评价了一句,仿佛只是确认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注意力又回到了激烈的星战画面上,“吊着命…也好。省得他们吃饱了撑的,整天琢磨些有的没的。” 他意有所指,显然想起了张处长那些“温暖”的暗示。
【明白!珩爷您放心,有咱们兜底,饿不死人!】系统立刻保证。
而在仅一墙之隔的95号西合院里,关于娄晓娥给“王特派员”当“生活助理”这件事,早己是暗流涌动,议论纷纷。寒冬似乎把人们都逼进了屋里,却关不住那些在炉火旁发酵的闲言碎语。
贾家。
贾张氏盘腿坐在热炕头,纳鞋底的锥子戳得格外用力,嘴里不停地叨叨:“呸!什么‘生活助理’?说得好听!不就是个伺候人的老妈子嘛!还是伺候那个…那个谁也摸不清路数的爷!” 她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嫉妒和不屑,“资本家的小姐,如今倒学会放下身段去巴结人了?我看啊,就是看人家王特派员本事大,想攀高枝儿!”
秦淮茹默默地坐在炕沿搓玉米粒,手指冻得通红。听到婆婆的话,她动作顿了一下,低声道:“妈,您别这么说。晓娥能有个正经工作…挺好的。王特派员…是好人。” 她想起王子珩随手给傻柱撑起的盛大婚礼,想起他一句话就改变了易家的命运,也想起了自己家沾光吃过的肉和糖。但心底深处,又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酸涩。娄晓娥离婚后,反而一步登天,接触到了她们这些人想都不敢想的人物和世界。而她秦淮茹,还在为了一口吃的、孩子的学费精打细算,在轧钢厂后勤部累死累活。
“好?好个屁!”贾张氏啐了一口,“你看她那神气劲儿!穿得人模狗样,天天往那小院跑!那院子是能随便进的?指不定在里面干些啥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听说啊,那王特派员年轻着呢,长得也好…” 她压低了声音,带着恶意的揣测,“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天天往单身男人院里钻…哼!能有什么好事儿?我看就是…”
“妈!”秦淮茹猛地提高了声音打断她,脸色有些发白,“您别瞎说!让王特派员听见了…” 她不敢想后果。许大茂的前车之鉴,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头。
贾张氏也似乎想起了什么,缩了缩脖子,嘟囔着:“我就在家说说…在外头又不说…”
中院,易家。
一大妈肚子己经显怀,裹着厚棉袄坐在炉子边烤火。易中海小心翼翼地给她腿上盖了条毯子,正是王子珩当初送的布料做的。
“老头子,你说…晓娥这工作,到底咋样?”一大妈轻声问,带着点担忧,“那小院…神神秘秘的。王特派员那人,看着和气,可那眼神…深得很。”
易中海拨弄着炉火,火光映着他深思的脸:“组织上安排的,自然有道理。晓娥稳重,读过书,比咱们院里的婆娘都强。让她去…合适。”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至于那小院…不该打听的别打听。王特派员做事,自有他的章法。你看他对咱们…够仁义了。” 他指的是双胞胎和源源不断的营养品。“晓娥只要本分做事,别像张婆子那样瞎琢磨,应该出不了岔子。这是她的造化。”
一大妈点点头,摸着肚子,感慨道:“是啊,要不是王特派员…咱家哪有这福气。晓娥…希望她也能沾沾福气吧。”
后院,刘家。
二大爷刘海中端着茶缸子,听着收音机里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论,心思却完全不在上面。他咂摸着嘴,对二大妈说:“啧,这娄晓娥…命是真好!许大茂那混蛋玩意儿滚蛋了,她倒攀上高枝儿了!‘生活助理’?听着就体面!肯定比在街道糊纸盒强百倍!工资少不了,指不定还能捞着啥好东西!你看她最近穿那呢子大衣,多精神!肯定是王特派员给的!”
二大妈一边补衣服,一边撇嘴:“体面?我看是伺候人的活儿!那王特派员是好伺候的主儿?你看光齐光福,在他跟前大气都不敢喘!娄晓娥再是读过书,到了那儿,不也得看人脸色?”
“你懂啥!”刘海中瞪了老伴一眼,“看谁的脸色?那是王特派员的脸色!多少人想凑上去看还没门路呢!光齐光福那是撞大运了!娄晓娥这也是撞大运!这要是…这要是能跟王特派员搭上更深的关系…” 他绿豆眼里闪烁着精明的光,“咱们光齐光福,不也跟着水涨船高?说不定…我这二大爷的位置,还能往上挪挪?” 他开始做起美梦。
前院,阎家。
三大爷阎埠贵戴着断了腿用胶布缠着的老花镜,就着昏暗的灯光在记账本上写写画画。三大妈在旁边唉声叹气:“这天儿冷的,柴火又涨价了…眼看要过年了,棒子面都不够…”
阎埠贵头也不抬:“省着点用!勒紧裤腰带!国家不都说了,困难是暂时的!” 他放下笔,推了推眼镜,话锋一转,“你们说…娄晓娥在王特派员那儿当差,能不能…给咱们院儿也谋点福利?你看傻柱结婚那会儿,全院跟着沾了多大光!又是肉又是酒又是稀罕果子…”
阎解成插嘴道:“爸,您想啥呢?人家那是工作!是组织安排的!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
“你懂什么!”阎埠贵瞪了儿子一眼,“事在人为嘛!晓娥这孩子心善,又在那个位置上,手指缝里漏点出来,就够咱们过个肥年了!解成媳妇,”他看向于丽,“你跟晓娥以前关系还行,找机会跟她唠唠,诉诉苦,就说家里实在困难…看能不能…咳,暗示暗示?”
于丽撇撇嘴:“我可不敢!您没看晓娥姐现在,虽然和气,可那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透着股…说不上来的劲儿。再说,那小院是随便能攀关系的?我可不想触王特派员的霉头!” 她想起傻柱婚礼上那排场,心里既羡慕又有点发怵。
阎埠贵被噎了一下,讪讪地继续拨弄算盘珠子:“唉…也是…那位爷的心思,谁敢猜?还是…再算计算计吧…”
娄晓娥本人呢?
她穿着王子珩让刘光齐“找”来的、厚实暖和的羊毛呢大衣(自然是从库房取出,在空地交给她),踩着崭新的棉皮鞋,每天准时出现在小院门口。在众人或羡慕、或嫉妒、或探究的目光注视下,推开那扇厚重的院门,走进那个神秘的世界。
她能感受到背后那些复杂的目光,尤其是贾张氏毫不掩饰的鄙夷和秦淮茹那欲言又止的复杂。但她只是挺首了背脊,目不斜视。她知道自己现在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什么,也深知那扇院门后的世界有多么深不可测。她谨记着自己的身份——一个被严格限定在青石板路和左侧空地上的“助理”。
她在院子里安静地做事,整理那些看不懂的图纸,记录下那些稀奇古怪的物品名称,偶尔在简易棚下尝试操作那些未来厨具(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王子珩通常只尝一口就皱眉让刘光齐去打包)。她递上饮料,传递消息,像个精准而沉默的零件。王子珩对她依旧疏离,偶尔投来的目光带着洞悉一切的玩味,那句“更有趣一点”的评价像烙印一样刻在她心里,让她在拘谨中又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悸动。
她知道院里的人在议论她,猜测她和小院里的秘密。她无从解释,也无需解释。这道院门,不仅隔绝了寒冬,也隔绝了两个世界。她站在界限的边缘,一面是充满烟火气与生存挣扎的西合院,一面是慵懒神秘、掌控着难以想象力量的核心禁区。而她,成了这界限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一个寒冷冬日里,让95号院所有人既羡慕又不敢深究的谜题。她裹紧了温暖的大衣,踏过覆霜的青石板路,身影消失在院门内,留下身后一院子的窃窃私语,在寒风中飘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