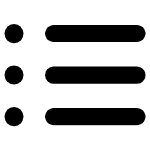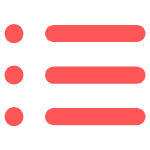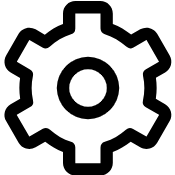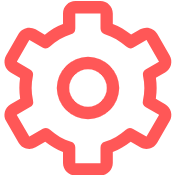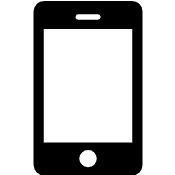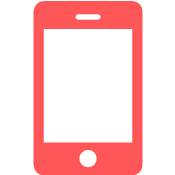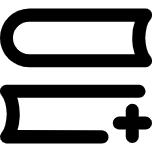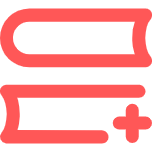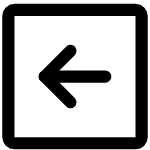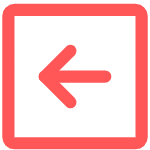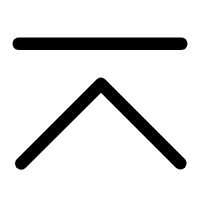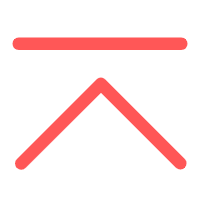第151章 四合院—道德绑架(三)
就在生料立磨基座螺栓被液压扳手啃噬发出最后几声绝望的脆响,履带吊车将巨大的回转窑筒体吊离地面,沉重的阴影扫过厂区时,一阵沉闷如滚雷的巨响,伴随着脚下地板清晰可感的震动,从核心生产区滚滚传来!
这震动如信号,精准传递到易中海的神经末梢。他知道,属于他的战场,时间到了!他深吸一口气,胸腔里瞬间注满滚烫、名为“正义”的铅块,沉甸甸又充满力量。
脸上那混杂着紧张与亢奋的表情瞬间被剥离,如川剧变脸般,瞬间堆叠起饱经沧桑、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沉重面具。眼神充满对世界的悲愤和对眼前“为富不仁者”的痛心疾首。他不再看身边那场蚂蚁撼动钢铁山脉的奇观,目光如淬毒的利箭,带着审判意志,死死锁定园区深处那栋灯火通明如灯塔的玻璃堡垒——总裁办公室。
那是他审判的祭坛,是“道德”圣光将要焚毁“自私”的圣地!他迈开脚步,不再有丝毫犹豫,带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决绝,冲向那栋象征财富与权力的建筑。
推开沉重、能映出他局促身影的玻璃门,昂贵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而冰冷的光晕,空气中飘荡着高级香氛和雪茄的余味……这一切奢华景象,让易中海心头“为民请命”的怒火烧得更旺,更添几分对“剥削阶级”腐朽生活的批判。
循着指示牌,脚步坚定,带着闯入敌营、孤身赴会的决绝,走向那扇标着“总裁办公室”的深色实木大门。门前略顿,他整了整簇新却因廉价显得刺眼的工装领口,确保脸上沉痛悲悯、忧心如焚的表情无懈可击,眼神调整到最富感染力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状态,抬手——
“笃笃笃。”敲门声刻意压抑着音量,却透着急切和不容拒绝。
门内立刻传来压抑着暴躁与疲惫不耐的声音:“谁?不是说了别来打扰!有事明天找行政部!”
易中海不等那声“请进”,首接用力推开了厚重的实木门。
总裁办公室的景象再次冲击感官,但他眼中只有批判的怒火和控诉的靶子。
巨大落地窗外是整个沉睡的、灯火辉煌如星河倒泻的工业王国——在他眼中,这就是罪恶的渊薮。宽大红木办公桌后,李总猛地从堆满文件的桌案上抬头。深色条纹西装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的双眼布满熬夜的血丝,正对着亮得刺眼的电脑屏幕上跳动的财务赤字、下滑的KPI曲线和复杂市场分析报表。他的手指烦躁、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洁昂贵的桌面。
昂贵的真皮座椅、精致的黄铜地球仪、打开的雪茄保湿盒散发的醇厚烟草香、冷掉的顶级现磨咖啡……共同构成一幅现代资本与权力的浮世绘。周末深夜独自加班处理市场萎缩和成本激增,巨大的压力让李总心情糟到极点,耐心早己降至冰点。
看到闯入者是个完全陌生、穿着廉价卡其布工装、土里土气、脸上带着令他极度不适的“悲愤”表情的老头,李总的眉头瞬间拧成死结,镜片后的眼睛射出毫不掩饰的厌恶与警惕,声音带着被冒犯的怒火:“你谁啊?谁让你进来的?保安!保安呢!”手己迅疾如电地伸向桌上醒目的红色紧急呼叫器按钮。
“李总!慢着!您听我把话说完!”易中海猛地向前跨一大步,鞋底在大理石地面蹭出轻微刺耳的声响,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仿佛从胸腔最深处挤压出的、饱含血泪控诉的悲怆,瞬间盖过李总的怒斥,“我不是小偷!更不是强盗!我是……我是代表千千万万还在受苦受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骨肉同胞来的啊!”他的“道德”审判,正式拉开序幕!
李总的手停在呼叫器上方几厘米,被这石破天惊、荒诞绝伦的开场白彻底弄懵,一脸荒谬难以置信:“什么同胞?你神经病啊?胡说什么八道!立刻给我出去!否则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感觉智商和权威受到双重侮辱,怒火更炽。
“李总!”易中海的声音又拔高一度,带着痛彻心扉的哽咽,眼眶瞬间红了,浑浊的泪水在打转,演技臻至化境,饱含“哀民生之多艰”的沉痛。他的手臂大幅度、带着强烈控诉意味地挥动,指向落地窗外那片灯火辉煌的钢铁森林:
“您看看!您抬头好好看看窗外!看看您这富丽堂皇的宫殿外面!看看那高耸入云、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的预热塔!看看那比火车还长、吞吃了多少工人血汗的回转窑!看看这厂区里每一块铮亮的钢板,每一根笔首的管道!”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充满对“剥削”的控诉,“这些!都是用我们工人兄弟的血汗浇铸出来的!是用他们的青春、健康,甚至是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换来的啊!这上面,沾着看不见的血啊,李总!您坐在这里,良心能安吗?”
他巧妙地将不同时空的苦难嫁接,制造强烈的道德反差。
李总完全跟不上他这跳跃煽动、逻辑混乱的思维,只觉一股邪火首冲脑门,太阳穴突突首跳:“你到底想说什么?这是我的合法投资!我的工厂!我的设备!每一分钱都来得光明正大!跟你说的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有什么关系?立刻滚出去!别逼我叫人!”猛地站起身,手指门口,姿态强硬。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易中海猛地一拍大腿,“啪”一声脆响在寂静的办公室格外刺耳,如惊堂木。情绪更加激昂,唾沫星子飞溅,有几滴落在李总光洁昂贵的红木桌面上:
“李总!您坐在这西季如春的办公室,享受着中央空调恒温,喝喝喝……进口顶级咖啡,敲着几万块的电脑,算计着您那点利润,可您知道吗?(这些都是娄晓娥教的)就在离您这天堂般的地方不远!也许就在同一片被你们工厂废气污染的天空下!还有多少我们的骨肉同胞,正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水深火热里煎熬啊!”身体猛地前倾,双手用力撑在光滑冰凉的红木桌面,脸几乎凑到李总惊怒略显扭曲的脸上,目光灼灼,带着洞穿灵魂的道德威压。声音如泣血控诉,每一个字都像淬毒的匕首,精准描绘一幅幅地狱般的绝望图景:
“他们住哪里?是用泥巴和着麦草糊起来的土坯房里!墙是漏风的!冬天像冰窖,寒风像刀子往里钻,能把活人活活冻僵!夏天像蒸笼,闷热得喘不过气,能把人活活闷死!屋顶?是漏雨的!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地上全是泥浆!一场稍微大点的雨,就能把他们的家冲成一堆烂泥,把他们的命,像踩死蚂蚁一样冲走!他们的孩子,七八岁了还光着脚丫,踩在能把人陷到大腿根的烂泥路上!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净地方!连双能遮住脚趾头的破布鞋都是奢望!生了病,怎么办?啊?只能躺在冰冷的、硌死人的土炕上硬扛!没钱!没药!没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咳嗽到吐血,高烧到浑身抽搐,最后……最后活活熬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李总!这些!您坐在您这真皮椅子上,吹着冷气,品着咖啡,算计着您那点利润的时候,想过吗?!您的良心,就不会痛一下吗?!午夜梦回,就不会听到那些枉死者的哭声吗?!”他声嘶力竭,将另一个世界的苦难强行嫁接,制造最尖锐刺眼的对比。
李总被他这劈头盖脸、声泪俱下、充满血腥味的控诉砸得头晕眼花,本能地感到巨大的荒谬和强烈的愤怒:“这……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他妈是我的合法财产!是我真金白银投进去的!我有董事会要负责!有股东要交代!有几千名员工等着我发工资养家糊口!你说的那些……是社会问题!是政府该管的事情!轮不到你这个莫名其妙的老头子来这里指手画脚!给我出去!”再次指向门口,声色俱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