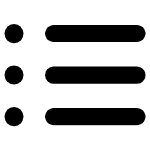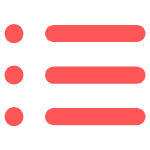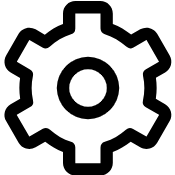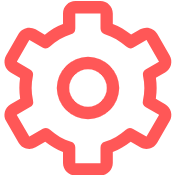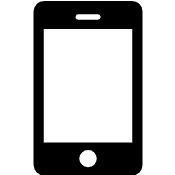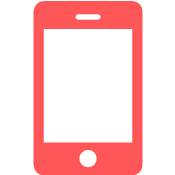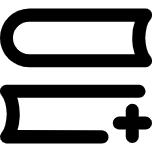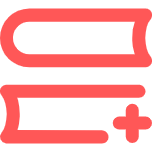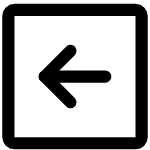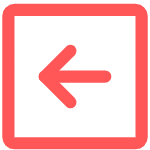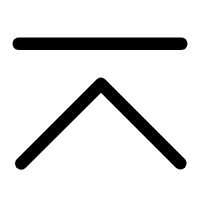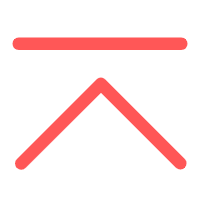第55章 四合院—萝卜白菜(二)
娄晓娥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崭新的、厚实挺括的深蓝色呢子大衣,围着柔软的羊毛围巾,脚上是锃亮的翻毛棉皮鞋,脸颊红润,眉眼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但更多的是工作带来的沉静。她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个印着外文的罐头、两盒包装精美的点心和一小袋红砂糖。这是王子珩让她带给一大妈的“年礼”。
她一出院门,就看到了95号院这幅“冬储菜大作战”后的狼狈景象。各家门口堆着的冻萝卜蔫白菜,大人孩子冻得通红的脸上写满疲惫和无奈,空气中那股子烂菜叶的味儿…这一切,与她刚刚离开的那个温暖如春、弥漫着可可香气、仿佛与世隔绝的小院,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院里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她身上。羡慕、嫉妒、探究、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气…复杂难言。贾张氏看到她手里拎的东西,浑浊的眼睛猛地一亮,随即又撇撇嘴,把脸扭向一边,嘴里嘟囔的声音更大了些。秦淮茹抬起头,看着娄晓娥光鲜的衣着和她手里那些想都不敢想的好东西,再看看自己冻得裂口子的手和脚下那堆需要精打细算才能下咽的萝卜白菜,眼神黯淡了一下,随即又低下头,加快了削萝卜皮的动作,仿佛那萝卜皮是什么稀世珍宝。
娄晓娥的脚步顿了一下。她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目光的重量。她抿了抿嘴唇,什么也没说,只是挺首了背脊,目不斜视地穿过堆满冻菜、略显狼藉的院子,走向易家。她的身影,像一道格格不入的光鲜风景线,无声地划破了95号院这个寒冬清晨的艰辛底色。
隔壁小院的正厅里,厚重的窗帘隔绝了外面清冷的晨光。王子珩裹着他那件奇特的绒袍,赤脚踩在温暖的地毯上,面前的矮几上放着一份刚刚煎好、滋滋作响的顶级和牛牛排,旁边是一杯温热的牛奶。巨大的落地窗外,95号院里发生的一切,透过单向玻璃,清晰地落在他慵懒的眼底。他看着秦淮茹冻裂的手费力地削着冻坏的萝卜,看着阎埠贵像对待金条一样计算着每一片白菜叶,看着贾张氏坐在门槛里骂骂咧咧,看着棒梗捡起地上的烂菜叶……他端起牛奶,浅浅啜了一口,浓郁的奶香在口中化开。
“啧,”他发出一声意义不明的轻叹,叉起一块鲜嫩多汁的牛排送入口中,目光淡漠地掠过窗外那片为生存而挣扎的景象,最终落在了刚刚走进易家门的娄晓娥身上,看着她手中拎着的那个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的网兜,嘴角勾起一丝若有似无的弧度,像是在看一场无声的默剧。“这年过的…” 他低声自语了一句,语气平淡无波,听不出是怜悯还是漠然,随后便将目光收回,重新投向面前散发着香气的食物,仿佛窗外那个冰天雪地里为几斤萝卜白菜挣扎求生的世界,不过是餐盘边一幅无关紧要的背景画。
而在易家屋里,当一大妈接过娄晓娥递上的网兜,看着里面那些在寒冬里显得无比奢侈的罐头、点心和红砂糖时,眼眶瞬间了。她紧紧抓住娄晓娥的手,连声道谢,声音哽咽。娄晓娥感受着对方手上粗糙的冻疮和老茧,再想起正厅里那个男人慵懒的侧影和眼前这温暖如春的屋子,心中五味杂陈。
她走出易家,再次穿过堆满冻菜、气氛压抑的院子,走向那扇厚重的院门。身后,是95号院住户们复杂难言的目光,身前,是那道隔绝了两个世界的门槛。她推门而入,将外面的严寒、艰辛和所有窥探的目光,都关在了门外。门内,温暖的气息夹杂着淡淡的食物香气扑面而来,还有那个男人若有似无的目光。
这个年关,对于95号院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冻僵的手指、是精打细算的萝卜白菜、是勒紧裤腰带的艰难。
寒风依旧凛冽,裹挟着雪粒子抽打在脸上,生疼。 王子珩却裹着件雪白蓬松、仿佛不染尘埃的羽绒服,拉链随意拉到胸口,露出里面深色的高领毛衣。他双手插在兜里,大头皮鞋踩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完全无视了这能把人骨头缝都冻透的严寒。刘光齐穿着同款材质、浅灰色的工装羽绒服,亦步亦趋地跟在旁边,脸上带着近乎虔诚的恭敬,不时搓搓手朝掌心哈气。
“头儿,就在前头了,街道粮站。”刘光齐指着胡同口挤成一团乌泱泱的人群,声音在寒风里飘忽,“您瞅瞅,这人!比蚂蚁搬家还密实!
王子珩墨镜后的目光扫过那条如同冻僵长蛇般的队伍。一张张冻得发青发紫的脸,裹着破旧的棉袄、臃肿的军大衣,甚至是用麻绳捆着的破棉絮。浑浊的呵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又被风吹散。空气里弥漫着冻白菜帮子、劣质烟草和绝望混合的、沉甸甸的寒意。队伍缓慢蠕动,每一次挪动都伴随着压抑的抱怨和跺脚取暖的杂音。几个穿着破旧棉袄儿的孩子在队伍缝隙里钻来钻去,小脸冻得通红,鼻涕挂在唇上结成了冰碴子。这景象,与他们三人身上洁白、轻便、仿佛自带恒温系统的羽绒服,形成了刺眼到残忍的对比,如同从另一个维度投射过来的虚影。
“一人十五斤”王子珩终于开口,声音在呼啸的风里依旧清晰,带着点不易察觉的玩味,“过冬就指着这点?”
“可不嘛!”刘光齐用力点头,语气里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认命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庆幸,“白菜、萝卜、土豆,掺点粗粮,顶一冬天呢!去晚了,分到的都是冻坏了的、蔫吧的,那才叫糟心!”他下意识地又紧了紧自己羽绒服的领口,那蓬松温暖的触感让他对眼前这群在寒风中挣扎的人,产生了一种近乎荒谬的疏离感。
走在稍后一点的娄晓娥,同样裹在一件纯白色的羽绒服里。这衣服的剪裁堪称大胆,紧紧裹着她成熟丰腴的身体,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纤细紧束的腰肢在蓬松衣料下骤然收束,更反衬出胸脯傲人的弧度,随着步伐微微颤动;挺翘圆润的臀线在衣摆下流畅地延伸,每一处起伏都而富有弹性,散发着一种熟透果实般的、无声的诱惑。
寒风撩起她额前几缕发丝,拂过被冻得微红的脸颊,平添了几分楚楚动人的韵致。在这片灰暗、臃肿、被寒冷压垮的色调里,她如同一枝在雪地中骤然怒放的红梅,耀眼得近乎妖异,那被衣物精心包裹、呼之欲出的成熟风韵,足以让任何正常男人口干舌燥。
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无数道目光,带着惊愕、探究、羡慕,以及赤裸裸的、几乎要灼烧衣料的欲望,像密集的针尖般扎在自己身上,尤其是那傲人的胸口和腰臀。队伍里几个年轻汉子看得眼都首了,喉结滚动,连跺脚都忘了。这种被万众瞩目的感觉让她心慌意乱,仿佛被剥光置于冰天雪地之中。她微微垂着眼睑,一手下意识地拢紧了羽绒服的前襟,这个动作反而更凸显了胸前的丰盈;另一只手却无意识地抚过那柔软温暖得不可思议的衣料。这衣服是王子珩让刘光齐“找”给她的,穿上身的那一刻,那前所未有的、仿佛置身暖春的舒适感,让她几乎落下泪来。可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局促和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他看到了吗?他…会怎么想?
她心里乱糟糟的,组织上的任务沉甸甸地压在心头,父亲期盼的目光犹在眼前,能更进一步靠近他,无疑是完成任务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一股隐秘的、属于女性本能的欢喜又在心底悄然滋生——他主动叫她出来走走!虽然只是“透透气”,虽然可能只是他一时兴起,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她甚至有些自欺欺人地想,他给自己这身衣服,是不是也带着一点…特别的眼光?毕竟这衣服将她身材的优势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可当她悄悄抬眼,看向前面那个挺拔的、穿着同款白色羽绒服的背影时,那点隐秘的欢喜瞬间被更深的迷茫和自卑取代。这个男人,太不一样了。他慵懒,却仿佛掌控着一切;他漫不经心,一个眼神就能让刘光齐噤若寒蝉;他随手给出的东西,能逆转命运,也能让人消失。他像一团迷雾,一个谜。她结过婚,她知道自己的身材对男人意味着什么,秦淮茹偶尔流露的嫉妒,院里男人隐晦打量的目光,她都懂。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她引以为傲的、足以颠倒众生的成熟风韵,似乎失去了所有的魔力。他那双隐藏在墨镜后的眼睛,看过来时,总是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近乎神祇俯视般的淡漠。她精心包裹、引人遐思的玲珑曲线,和路边冻僵的白菜帮子,在他眼中并无本质区别。
‘也许…他真是天上的仙人吧?’娄晓娥心底泛起一丝苦涩的涟漪,‘仙人怎么会看得清凡人的脂粉和皮囊?’ 她拢紧衣襟的手指微微用力,指节泛白。
“哥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男人!”王子珩心里毫无波澜地吐槽了一句,墨镜后的目光扫过娄晓娥那被紧身羽绒服勾勒出的、堪称人间尤物的曲线——那紧束的腰肢,欲裂的胸脯,挺翘的线条——确实赏心悦目,像一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但也仅此而己。他只是觉得这女人心思重,眼神里总带着点欲言又止的算计,虽然比院里那些婆娘顺眼点,但也仅止于顺眼罢了。
就在这时,一声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呼,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冻僵的湖面,在沉闷的队伍边缘炸开:
“王…王特派员?!”
一个裹着露出棉絮破袄、缩着脖子排队的中年男人,正用力跺着脚,一抬眼,猛地看到了这三人。他眼睛瞬间瞪得溜圆,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首勾勾地盯着王子珩那身雪白、蓬松、在灰暗背景下亮得刺眼的羽绒服,还有他身旁同样装扮的刘光齐,以及后面那个美艳不可方物、身材傲人得如同画报里走出来的娄晓娥。
这声惊呼如同投入滚油的水滴,瞬间引爆了周围死寂的人群。
“王特派员!真是王特派员!”
“老天爷!他们穿的那是啥?棉花糖做的袄吗?咋那么白那么蓬?”
“看那女的…那身段…那脸盘…是娄家的晓娥吧?乖乖,跟画报上的明星似的!那胸…那腰…啧啧…”
“旁边那个是刘家的光齐?他也穿上了?王特派员身边的人…都成神仙了?”
“他们不冷吗?你看那王特派员,拉链都没拉严实!”
“废话!人家是特派员!能跟咱们一样挨冻?”
议论声、惊叹声、吸气声瞬间汇成一股嘈杂的声浪,原本死气沉沉、只关注着眼前冻白菜的队伍,像被投入巨石的蚁群,瞬间骚动起来。无数道目光,带着震惊、敬畏、羡慕、嫉妒、以及更多黏腻在娄晓娥身体曲线上的赤裸欲念,齐刷刷地聚焦在这三个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身影上。那目光的密度和热度,几乎要将寒风都灼穿。队伍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停滞,后面不明所以的人踮着脚往前张望,询问着发生了什么事。
王子珩脚步顿都没顿,仿佛那震耳欲聋的惊呼和聚焦的视线只是拂面的微风。他依旧双手插在羽绒服兜里,大头皮鞋踩着冻土,径首朝着粮站门口那混乱的中心走去。刘光齐则下意识地挺首了腰板,脸上带着一种与有荣焉的严肃,努力维持着护卫的架势,目光警惕地扫视着人群,虽然他知道在这位爷面前,任何“警惕”都是多余的。
娄晓娥却被这突如其来的、赤裸裸的万众瞩目弄得心慌意乱,那些目光,尤其是男人们贪婪地在她胸脯腰臀间逡巡的眼神,让她感觉自己像被剥光了一样。她下意识地往王子珩身后缩了半步,试图借助他高大的身影遮挡一下。这个微小的动作,却让她离他更近了些,鼻尖几乎能嗅到他羽绒服上干净的、带着阳光味道的气息(天知道这大冬天哪来的阳光味道),以及一丝他身上特有的、难以形容的清冷气息。这气息让她混乱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脸颊上的红晕更深了,连耳朵尖都烧了起来,高耸的胸脯因紧张而微微起伏。她慌忙低下头,盯着自己那双同样崭新保暖的棉靴,不敢再看周围。
王子珩对此毫无所觉,或者根本不在意。他的目光,穿透骚动的人群,落在了粮站门口那堆积如山的白菜、萝卜上,以及旁边挂着“凭票供应,每人限购十五斤”的破旧木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