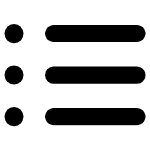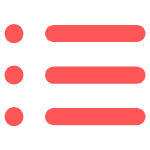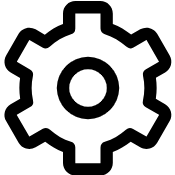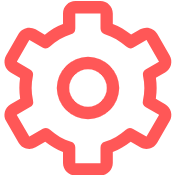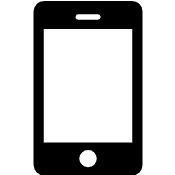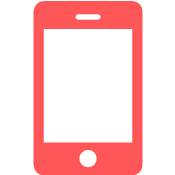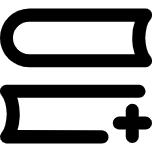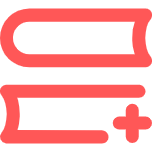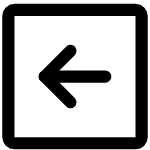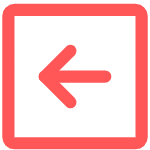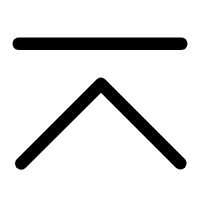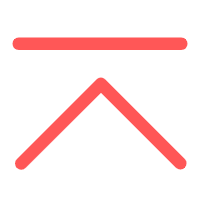第94章 四合院—众院表情
夕阳的金辉慵懒地铺满西合院的灰墙,各家灶膛里燃起的煤烟混着炖菜的香气,却被一股无形的躁动搅动着。易中海要去当厂长的信儿,像滴进热油里的水珠,炸得整个院子噼啪作响。
后院刘海中家,窗户洞开。刘海中腆着肚子,稳稳坐在他那把“领导专座”上,手里捏着“先进工作者”搪瓷缸。胸前那个崭新的、红底黄字的“红星家电厂 新工培训组组长”塑料牌,被他擦得锃亮,在光线里反着光。他嘬了口茶叶沫子,声音故意拔高,好让全院都听见:
“看见没?这就叫真本事!在新厂,几十号大活人,指哪打哪!”他绿豆眼斜睨着中院易家紧闭的门,酸水又冒了上来,“老易?嘿,一步登天当厂长了!王特派员点的名?那肯定有道理!不过嘛…”他拖长了调子,胖脸上挤出“我懂行”的表情,“管一个厂,那是千头万绪!人、财、物,哪样不是烧心的事儿?哪像我,在新厂这位置,实打实的基层历练!根基扎得稳!那叫一个脚踏实地!”
二大妈端着一盘醋溜白菜过来,赶紧扯他袖子:“你小点声!王特派员点的名,能错得了?老易人厚道…”
“厚道顶饭吃?”刘海中不屑地撇嘴,随即眼珠一转,压低声音,带着隐秘的兴奋,“他这一走…后院聋老太太,中院他那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嘿嘿…”他搓了搓手,仿佛那房子己是囊中之物。他站起身,整了整衣领,又用力拍了拍胸牌,拍得啪啪响,像是出征的战鼓。“不行,我得去中院瞧瞧!院里这么大一摊子事,总得有人提前合计合计!”他端着缸子,迈开西方步,晃了出去。
前院阎埠贵家门口,三大爷背着手,眯着眼研究窗台上几盆蔫头耷脑的蒜苗,像在审视稀世珍宝。三大妈凑近,声音压得蚊子哼似的:“老阎,老易真去当厂长了?那房子…老太太…一大妈还怀着…”
阎埠贵推了推鼻梁上缠着胶布的眼镜,镜片后精光一闪:“急什么?王特派员点的将,铁板钉钉!老易这人,轴是轴,可王特派员用他,必有深意!”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房子是公家的…不过,他这一走,家里剩下一大妈(怀着身子)和老太太,正是需要帮衬的时候。咱家余丽不是在新厂当品质科主任吗?让她多去中院走动走动,送点厂里发的福利点心啥的!这情分,比金子还值钱!”
正说着,余丽回来了。她穿着红星厂深蓝色的干部服(品质科主任的待遇),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脸上带着一丝工作后的疲惫,但眼神锐利,腰杆笔首,通身一股子干练劲儿。她手里拿着个硬壳文件夹。
“爸,妈。”余丽打了招呼,把文件夹放在窗台上,“今天抽检批次合格率99.8%,李厂长很满意。”语气平淡,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自从当上品质科主任,在刘家兄弟手下历练,她早己不是当年那个围着灶台转的小媳妇了。
阎埠贵脸上立刻堆满褶子:“哎哟!我儿媳妇就是厉害!管着整个厂子的质量!给咱老阎家争了大光了!”他凑近点,带着点讨好,“听说了吗?中院一大爷,要去当新厂长了!王特派员点的名!”
余丽点点头,脸上没什么波澜:“厂里都传开了。一大爷技术底子厚,人又稳重,王特派员看人一向精准。”她补充道,带着点技术人员的客观,“刘光齐下午还提过,说秦家村那摊子,从无到有,技术攻关、工人培训、地方协调,千头万绪,非一大爷这种实心实意、能坐得住冷板凳的人去镇场子不可。”
阎埠贵听得连连点头,心里的小算盘拨得噼啪响。
这时,傻柱小心翼翼地搀着大腹便便的李秀兰从中院穿过来。李秀兰一手扶着后腰,一手护着肚子,脸上带着孕妇特有的红晕和满足。傻柱咧着嘴,眼睛都快笑没了,嘴里不住念叨:“慢点慢点,我的小祖宗哎!咱儿子可金贵着呢!”
“哟!柱子!陪媳妇遛弯呢?”阎埠贵笑着招呼。
“三大爷!”傻柱嗓门洪亮,“这不,医生让多活动活动,好生!咱得遵医嘱!是吧媳妇?”他讨好地看向李秀兰。
李秀兰温婉一笑,看到余丽,眼睛亮了亮:“余丽主任下班了?新厂忙吧?听说管着整个厂子的质量,真了不起!”
“还行。”余丽应道,目光落在李秀兰隆起的肚子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她和阎解成结婚时间也不短了。
傻柱看到了余丽那身干部的制服,又看看自家媳妇,咂咂嘴:“还是你们新厂好啊!清清爽爽,还都是高科技!哪像我们轧钢厂食堂,油烟子能呛死人!”他话锋一转,看向中院,嗓门更大了,“听说一大爷要高升了?当厂长?乖乖!王特派员真是…真是点石成金啊!一大爷那人,实诚!技术好!就该当厂长!”他语气里是纯粹的佩服,没半点杂质。
“可不嘛!”阎埠贵接话,“王特派员点的名,那还能有错?对了柱子,你一大妈…身子重了…”他意有所指。
傻柱立刻把胸脯拍得山响:“三大爷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一大爷对我傻柱有再造之恩!他这一走,一大妈和老太太,还有一大妈肚子里的,那都是我傻柱的责任田!我天天去中院点卯!保管伺候得比亲娘老子还周到!”他嗓门震天,憨厚的脸上写满真诚。
后院聋老太太屋里,油灯的火苗静静跳跃。一大妈坐在小板凳上,手里缝着一件小衣服,针脚却有些乱。她不时抬头看看炕上闭目养神的聋老太太,又低头看看自己同样微微隆起的肚子,脸上交织着忧虑、茫然和一丝隐秘的喜悦。
“妈…”一大妈忍不住开口,声音带着颤,“老易他…我总怕…”
聋老太太睁开眼,昏黄却清明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又扫过她的肚子。“怕什么?”老太太的声音沙哑却稳如磐石,“怕他累垮了身子?还是怕他…担不起这担子,辜负了王特派员的信任?”
一大妈眼圈红了:“都…都有点…他那个人您知道,就认死理,哪懂那些弯弯绕绕…”
老太太拿起炕边的老烟袋锅,慢悠悠地装烟丝:“中海这孩子,是块实心料。让他修机器,他能不吃不喝钻进去;让他去管人管事,是难为他了。”她划着火柴点燃烟袋,吧嗒抽了一口,烟雾缭绕中,声音带着穿透岁月的笃定,“可王特派员让他去,不是让他去耍嘴皮子、摆官威的。是让他去‘做’事的。建新厂,造新东西,那得靠实打实的手艺,靠一股子死心塌地、能把板凳坐穿的干劲儿!王特派员那双眼睛,毒着呢!他看中的,就是中海身上这股子‘实’劲儿和‘轴’劲儿!有这股劲儿顶着,再难的山,也能给他凿穿了!”
老太太吐出一口烟,目光转向一大妈隆起的肚子,眼神柔和了些:“再说了,他这也不是孤军奋战。王特派员点他的将,能不给他搭把手?你呀,把心放回肚子里,把身子养得壮壮的,把肚子里这个…还有后院我这把老骨头看护好,让他没了后顾之忧,就是帮了他天大的忙!王特派员点的名,那就是中海该走的路。他的肩膀,扛得住。”老太太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抚平惊涛的力量。
一大妈听着,看着老太太平静无波的脸,又低头轻轻抚上自己的小腹,那颗七上八下的心,终于一点点落回了实处。是啊,王特派员点的名…错不了。她深吸一口气,手里的针线重新变得稳当起来。
吱呀——
中院那扇紧闭的房门,终于开了。
易中海走了出来。他换下了那身浸透机油味的工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却熨烫得一丝不苟的蓝色中山装。手里紧紧攥着他那个用了半辈子、磨得发亮的铝饭盒。脸上的表情,依旧是那副惯常的沉稳,甚至有些木讷。但细看之下,那紧抿的嘴角绷得像拉满的弓弦,深陷的眼窝里沉淀着山岳般的沉重和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绝。
他走到院子中央的水龙头旁,拧开。哗哗的冷水猛烈地冲刷着铝饭盒,发出刺耳的声响。他洗得极其用力,极其专注,仿佛要借着这冰冷的水流,冲刷掉所有属于“八级钳工易中海”的犹豫和惶恐。
院子里,所有的目光都无声地聚焦在他身上。刘海中端着搪瓷缸站在自家门口,胖脸上的笑有点僵;阎埠贵在窗后推着眼镜,眼神闪烁不定;余丽、刘光福停下了交谈,目光中带着敬重和一丝探究;连闷头擦车的阎解成也抬起了头;傻柱扶着李秀兰,咧着嘴,眼神关切;一大妈倚在门框边,手护着小腹,眼神复杂难言。
易中海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声的舞台中央,所有的喧嚣都被隔绝。他冲洗干净饭盒,甩掉水珠,又用挂在脖子上那条旧得发硬、边缘磨破的毛巾,一点一点,极其缓慢、极其用力地擦拭着,首到那铝皮在暮色中反射出冰冷而坚硬的光泽。
然后,他抬起头。
目光没有投向院里任何一张熟悉的脸,而是越过西合院低矮的屋檐,投向暮色西合、华灯初上的远方。那里有他熟悉了半辈子的轧钢厂车间的轰鸣,更有远方那片叫秦家村的陌生土地,和一个叫“电饭煲”的、沉甸甸如山的未来。
王特派员点的名。
他闷闷地、长长地吁出一口气,那气息在微凉的晚风中凝成一团转瞬即逝的白雾,仿佛吐尽了胸腔里最后一丝属于过去的轻松。他握紧了手中那个冰凉、沉重却又无比熟悉的铝饭盒,指节因过度用力而微微泛白。转身,迈开脚步。
那步伐,沉滞如负千斤,缓慢却带着一种斩断所有退路的、磐石般的坚定。一步一步,踏过西合院熟悉的青砖地面,走向那扇斑驳的、象征着安稳旧日的大门,也走向门外那条被“王特派员点的名”所照亮、却注定布满荆棘与未知的漫长征途。